白遼士周年

周年紀念是「回顧過去,展望未來」的時機。今年是法國作曲家白遼士(Hector Berlioz,1803–69)逝世一百五十周年,欲知「世界不斷進步」是否屬實,不妨回顧一下過去的「回顧與展望」罷。大史家巴森(Jacques Barzun)乃重要的白遼士學者,於 1970 年發表紀念該作曲家逝世百周年的文章1(見附圖);到了 2003 年,同一學者紀念同一作曲家誕辰二百周年的文章2刊出,那時他已經九十五歲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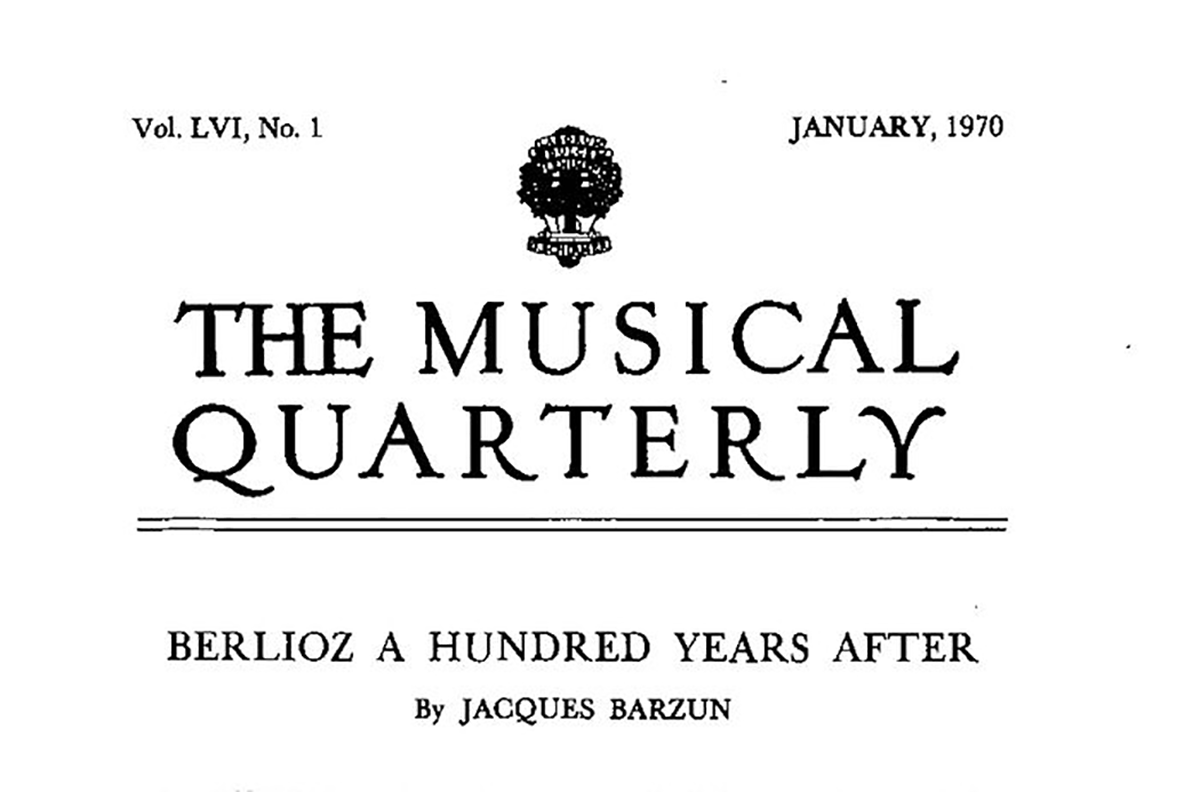
世人在上世紀中之「重新發現」白遼士,大大得力於巴森為他寫成的千頁傳記,謙謹的作者自己在那些紀念文章裏當然隻字不提。有一個現象,他卻不禁在相隔逾卅載的兩篇文章裏一提再提,那就是人們因白遼士替其《幻想交響曲》等作品寫過「導賞」文字,而認為他發明了一種需要聽者先閱讀一些甚麼才可欣賞的音樂,即所謂「標題音樂」(programme music)。此外,白遼士素來備受樂迷稱揚的,還有其管弦樂團配器呢——彷彿沒有動人故事解說或出格樂器音色,他的作品便一無是處似的。
巴森直言這些都如同瞎子摸象,恰恰顯示人們對白遼士音樂獨特之處,其實不甚了了。此所以在 1969 年、2003 年,乃至今時今日,人們談及這位作曲家時,仍然會以「奇怪」及各式各樣的同義詞形容之。論者說他「奇怪」,很多時都只表示了他們並不瞭解他;也許他跟那些「可瞭解」、「不奇怪」的作曲家太不同了,惟論者對他之殊異多又顢顢頇頇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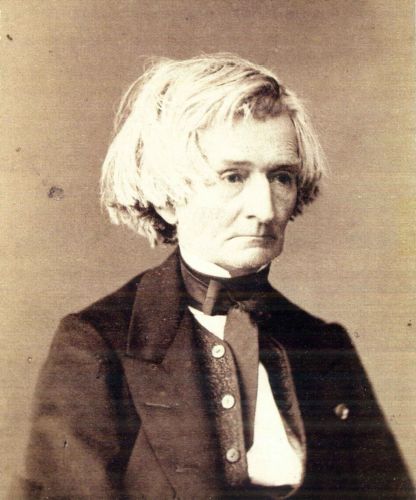
白遼士無疑於音樂的許多方面都大有創新。他更是個文人,一生著作頗豐,而且十分精采。只是他厭惡「理論」,未曾詳細而系統地介紹其音樂語言及美學,且不屑如華格納般直接作自我宣傳,否則他必定更為世人所瞭解,並更享生前身後名。白遼士沒有做的,巴森在五十年前的文章提醒學者辦妥:大量分析研究,探討白遼士音樂之構成元素。此類「技術含量高」的探討於近年甚有進展,對相關作品的鑒賞頗有幫助。可是一般音樂愛好者,有多少正在享受這些研究成果?未來的情況又會怎麼樣?
與其只是「展望」,不如嘗試帶來那怕只是一丁點兒改變罷。下次略談白遼士獨樹一幟的音樂風格特徵。
1 “Berlioz a Hundred Years After,” The Musical Quarterly 56, no. 1.
2 “Fourteen Points about Berlioz and the Public, or Why There Is Still a Berlioz Problem,” in Berlioz: Past, Present, Future, ed. Peter Bloom (Rochester: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).

3月2-3日(六、日)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
法國世紀樂團:白遼士150
白遼士(1803-1869)開啟了法國浪漫主義之門。適逢作曲家逝世150週年,法國世紀樂團將以十九世紀樂器原聲演繹白遼士作品:首場奏出為人熟悉的《幻想交響曲》及鮮有上演的「後傳」《雷里奧》,次場則有滿載文學及戲劇靈感的交響曲及歌劇序曲。
曲目詳情